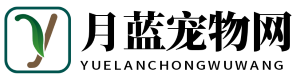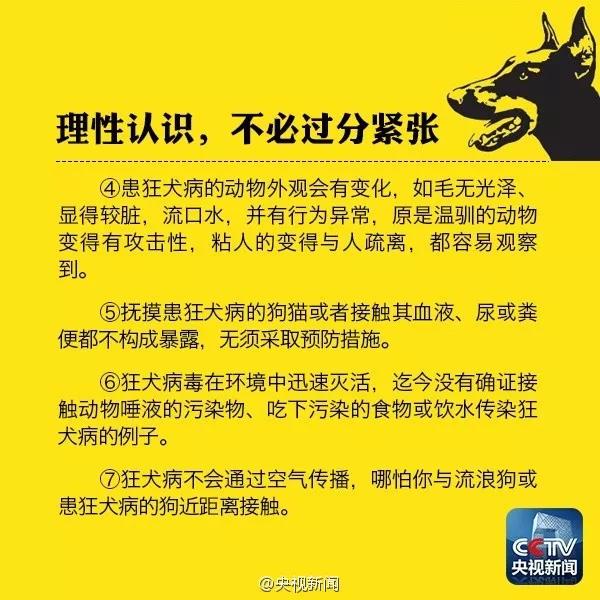一座四五里长的堤坝状土丘,从高到低、从宽到窄,笔直伸入湖中,形成一个坝状的湖口。 水天一色,远远望去,就像是肉中的一根朦胧的刺,尴尬难受; 又像一只手臂在湖中摸索着什么。
靠近湖岸,长长的山坡旁散落着几栋房屋。 那一年,他们都聚集在半里外的平坝,只留下一栋临湖三砖青瓦的老房子,孤零零地留在那里。 该湖直通长江。 有一年,一个小康之家的男人带着他的小妾带着家里的东西,从湖口乘船逃走了。 他的妻子在这里建造了这座房子,每天仰望着湖水,期盼着丈夫的归来。 有一天,她觉得自己不能再等了,就悄悄消失在湖里。 从那以后就没有人住过这所房子了。 直到那天,队长派人把已经老旧的房子收拾干净,又迎来了三女四男七位年轻的知识分子,这里才变得有些热闹。
湖区田多、幅员辽阔、人烟稀少、劳动强度大。 每逢农忙时节,所有壮士男女都会累得趴着睡觉,鸡鸣狗叫全然不觉。 几个知青。 不久,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加入了父亲的老战友的队伍。 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生病了,回到了城市。 还有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每天一起哭、一起睡。 他们也挺着大肚子,抱在一起哭。 然。 只剩下一个叫任武胜的男子,默默地住在那所房子里。
那人养了一条狗,是母的,除了四蹄之外全身都是黑的,额头上有一圈圆白的毛。 如果是马,叫“踏雪无痕”、“万里灯火”,那一定是好马。 不过,狗也很聪明。 每天晚上天黑的时候,只要有时间或者干农活不太累,狗就会拉起自制的二胡,奏出哭声、呻吟声、口哨声的曲调。 一切都寂静无声,那声音,在湖面上滚动,在田野里跳跃,显得叛逆而轻浮。 一首很长很长的歌,每天播放,永不改变。 这时,狗就会趴在狗的脚边,垂着耳朵,闭着眼睛,静静地听着。
任无生本意是“一日三省吾身”。 荆楚人称之为“人未醒”、“人未明”。 这些话是不雅且伤人的。 每个人都称他“无辜”,狗“不无辜”,无论是名义上还是耻辱。 打电话给他,他微笑着。 狗的情况并非如此。 当它叫的时候,它就叫,它越叫,它越叫,它越叫,它越叫。 村里的每个人都听到了那个人演奏的歌曲,但他们听不懂。 有的觉得有趣,就问那人:青青,这是歌还是戏? 男人笑了笑,没有回答。 还有人说这就像杀鸡一样,吱吱作响。 大家又笑了,你也笑了,没有生气。 队长还是很好的:他在他演奏的歌曲中是无辜的,但我们谁都不是。 有人嘘声:你就是狗! 大家都狂笑起来。 这次狗没有叫。
我不知道狗是否听得懂这首歌,但并不是所有的村民都听得懂。 不过,一个人应该是明白的。 每天晚上,队伍干完活后,会有一个十七、十八岁的女孩赶着队伍的牛到湖口附近吃草。 农家女儿,脸色红黑相间,七十八岁已是圆润凹凸不平; 有什么东西就要从破旧的衣服背后爆出来,弄得衣服吱吱作响。 喜悦、喜悦、怨恨、悲伤、悲伤、悲伤……有时面如桃花,有时满面泪痕。 只要歌曲响起,她就会坐下来听,一动不动。 直到歌声结束,她每天早晚都赶着牛回家,不提饥寒交迫。
壬午州知她为春蚕、秋蛾,人们称她为“秋蛾”。 两人工作时经常见面,但从未说过话。 最多只是点头微笑。 有时他也觉得奇怪,十七、十八岁的女孩子一般不放牛; 而他们全身的衣服都打了又补,破破烂烂的,仿佛只要用力,整个人都会暴露出来。 来。 那天下着大雨,她来避雨。 他问她。 她说:对于富农子弟来说,放牛是一种转变; 如果穷得买不起衣服,上面仍然是她母亲的嫁妆。 他发现后,一有时间就帮她照看牛。 回到城里,他向姐姐们要了一些旧衣服,悄悄送给了她。 衣服虽然旧了,但一穿上,她的美就突显出来,让他低下头,眸光璀璨。
那天,“双劫”时天气太热,他累得差点脱水。 湖边常停有几队有船头、有篷的小船,可供住宿和遮风挡雨。 等他下班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他下了船去湖里洗澡。 一入水,他就感觉身体没有力气了。 他连喊一声“结束了,结束了”的力气都没有了。 他默默地念诵着,慢慢地沉入湖底……不知道过了多久,他醒了,天上布满了星星,没有月亮。 她抱着他,静静地躺在船篷里,一言不发。 良久之后,他如狼嚎一般,将自己搂在她的怀里,抱着她,放声大哭……
那天晚上,没有风,湖面上却掀起一波又一波的猛浪,时而迸发出一串串美丽的水珠,绚丽地向四面八方散开,然后轻轻落下,融进湖里; 似乎还听见一阵阵闷雷般的声音和狼豹般的嚎叫声——船悄悄地转过头去。
狗先是呜呜叫了一会儿,然后就开始在岸边欢快地玩耍,狂奔、狂喷。
一致的好评让他在公社第一次有机会被招进工厂。 那个工厂在山里,那里有最纯正的中国菩萨。 进厂前,队员们给他带来了酒菜送行,室内洋溢着多年难得一见的欢乐和喜庆气氛。 他和队长等人一起疯狂喝酒。 一口气喝了三斤,差点把船长和他的朋友们吓瞎了。 他们立即以半神半神的目光望向他,询问他有什么要求,并答应一定会答应。 他说:“我走后,邱墨就住在这个房子里,家里的一切都属于邱墨。”说完,他又拿起了二胡,发出了叽叽喳喳的声音。 渐渐地,人散了,只剩下他、她和狗。
天快亮了,邱墨和狗已经送他去了公交车站。 他松开了邱漠的手,蹲下来抚摸着小狗,说道:“你留在这儿,替我照顾好她,我有时间就回来。” 看着你。 狗叫了六声:别担心,我知道!
修路、盖房子、安装设备造汽车……靠着勤奋和努力,他一年比一年进步。 转眼三年过去了,他的父母带了一个女孩到工厂做他的妻子。 当婚礼圆满的时候,他的心突然一阵揪痛,他突然想起了她。 这三年来,他给她送过钱、送过礼物,却都被退回了; 他写了很多信,虽然没有回信,但也没有收到她的回信。 乘车乘船行了几天,才跑进屋里。 狗远远地走到他面前,把腿搭在他的肩膀上,不肯下来。 一到家,就看到不会拉二胡的她,把二胡当作玩具,叽叽喳喳地逗弄着一个两岁左右的小男孩。 看到他,她惊呼了一声,旋即回过神来,拉着他坐下,给他倒茶倒水,询问他的近况。 他说,你结婚了吗? 这是你的孩子吗? 她脸上立刻浮现出羞涩的幸福红晕,她指了指他,又指了指孩子:一对两个一模一样的红薯……他明白了,抱起孩子,一会儿笑,一会儿哭。 。 他告诉了她一切,她也告诉了他一切:她怀孕了,她的父母把她赶出了家门,她不得不住在这个房子里,她过得很艰难。 他说,我回去离婚,带你去工厂! 她说:如果你敢这么做,毁了你的前程,我就抱着儿子跳河里。
他无奈地离开了。 她走的时候,没有送走他,也没有送走那只狗。 她恶狠狠地盯着他,哀嚎着、咆哮着,想要咬他。
与往常一样,金钱和物品将被退回,但信件将不会得到答复。 妻子从母亲那里知道了这件事,脸色沉下来之后就没有再挂电话,这也是无奈。 十几年后,他已经是七品厂的厂长了。 工厂要扩建,从山区搬到长江边。 他抓住机会去见她。 还没到家,狗就疯狂地冲到他身边,咬得他流血。 门没锁,锁上,推开:他的东西还在,二胡还挂在原处。 “邱漠,你在哪里……”他的哭声撕心裂肺,让他浑身发抖。 老队长无奈,只好过来告诉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她和她的母亲将不再在这个房间里。 有的说他们走了,有的说他们投湖了……
当晚,他又哭又叫,疯狂地弹奏着刚刚换上新琴弦的二胡,疯狂地无视日月和时间。 某个时候,他的妻子竟然出现在房间里,狠狠打了他一巴掌,然后就离开了。 当他离开的时候,狗刚想动一下,就摇摇晃晃地躺了下来,就没有再动了。
抛弃妻子、喜新厌旧、有旧情人……他的事业结束了。 门前没有车辆,儿子摔门离开,女儿骂他是老混混。 为了逼他离婚离家,他的离婚妻子居然勾搭上了一个在广场上扭着水桶腰只能点头弯腰的狗一样的中年男人。 她还故意把他带回家,在他面前摸摸、蹭蹭。 去……
他终于明白自己要去哪里了,拿着退休工资卡,回到屋里,收拾好东西,安顿下来。队长让几个年轻人给他送来了电线,这让老房子在晚上显得非常明亮。 他还给他带来了一只与“步青”相同但不同的大狗,并告诉他老狗已经死了。 现在,这是它仅存的后代了。 他还说,有人在外面看到了一个像秋蛾子一样的女人,但他们只是没有看到她的权利……
每天晚上,关灯后,他都会在黑暗中拉二胡。 还是一样的曲调、曲调、节奏,而且还是那么长。 那声音漂浮在湖面上,荡漾着田野,显得深沉而沉重。 传得很远,传到了左村右湾:打麻将的不再堆输赢了,不敬的儿媳妇羞得满脸通红,无耻的骗子打了自己一巴掌,村里的两个人吵架了,想离婚。 寇子听完这首音乐,不再争吵,听着,紧紧地拥抱着她,睡着了。 还有那些下班回来的男人和女人。 听完这首歌,他们不再想去远行……
那所房子仍然坐落在孤独的湖口; 那个男人每天晚上仍然拉着那曲儿; 那只狗每天晚上仍然趴在他脚边陪伴他。